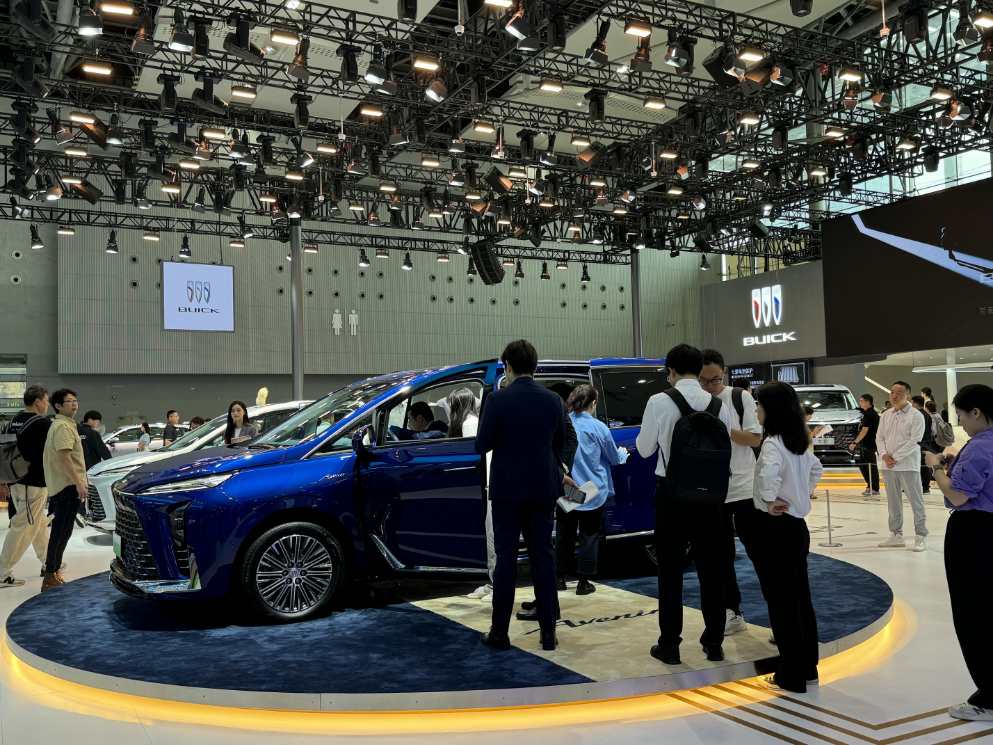随笔 | 品“封城日记”,穿越虚构与纪实
【导语 :读茨威格的纪实作品,看鲁迅杂文,品封城日记,就有了对历史的穿越,反观虚构的无力和苍白。】
撰文|颜光明、编辑|钱 蕾
在疫情之下收到友人寄来的《人类的群星闪耀》一书。我马上从书架上找出1983年的《斯·茨威格短篇小说选》。这让我重温了自己也看到了历史。
有人说,八十年代是文学激情的年代。记得当时购买茨威格小说时,文坛充斥的都是复活的名字,时钟还回荡在旧时的光阴里,不肯退去,依然离不开鲁郭茅巴老曹的庇护。新生代们在懵懂之中不满足已有的获取,开始追随尚未流行的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玩起了先锋和前卫。不过在众多的流派中,我还是欣赏茨威格,因为他的视角总是给人以人性的悲悯,温润中的惆怅。三十余年过后,看了徐静蕾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证实了我对茨威格小说的感觉被岁月淘洗之后还有共鸣。
同样,在疫情闲闷时,翻阅《成长初始革命年》(创作之外的思想札记),有了与时代同步的感触。王安忆对自己的清醒透射出智慧的高冷。她说:“以虚构为职业的人也许不该在现实中多说话,因为我们常常混淆真伪,‘想当然’错成‘所以然’。就像禅说,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所以,拿起《人类的群星闪耀》这本书时这才发现睿智背后的力量远不止思想,还有不屈的人格。茨威格是一位在取得举世公认的大作家,他却这样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冲淡或者加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内外真实性并改变人物的真正内心世界,因为历史本身在那些非常时刻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
这就不能不震撼。一个从文学激荡年代过来的人,以虚构为业,并以此传道授业,看淡江湖,选择了“不能说”,以虚构代言,有了名士的清雅。一个在昏暗年代选择非虚构的方式来记述悲歌,让群星闪耀,以证明“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
他们相向而行,各自听从内心的选择,一个只写“不能说”,一个转型“先走了”。所以,读他们的作品都有点累,赶不走压抑的郁闷。相较于文学而言,茨威格的非虚构要比他的小说更加出名,经久不衰,祭奠了自己的“遗言”——“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看到黎明!而我,一个过于性急的人,先走了。”
这就让我想起上个世纪末,京城一位我所敬重的文化老人托我带一本西塞罗的书给沪上一位名家,那份郑重其事,令我感动,彼此心照不宣,却心心相应。后来我自己也买了这本书,读后大悟,再读茨威格的西塞罗,才知思想的力量为何令一些人害怕。深夜里,读朋友圈的“封城日记”,常有标注提醒,马上看。微群疯转。不长的文章,每次都在10万+,封和删都没用。日记中不少话都是大白话,也是常识和真话,反而成了网络上的金句。比如“灾难即将结束。朋友们,千万不要跟我谈胜利。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
这就让我想起了鲁迅。它也是敢说话的人,却又常用曲笔来虚构,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表现方式。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嫂”等。有人考证,“阿Q”就有唐吉坷德的影子。说明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借鉴了西方创作技巧。他曾说过“狂人日记”写得有点幼稚,但到了“祥林嫂”,就有了本土化的圆熟。不管这么看,鲁迅虚构的经验是抓住了“悲剧”的要点,挖掘出震撼。他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茨威格回忆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就难怪高尔基在看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写信给茨威格说,“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他悲痛的心曲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羞耻地哭了起来。”看来这都与悲剧因素有关。
看了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打动人的还是电影的主题曲,“琵琶语”。这是中国的壳,西洋的魂,却是那样的凄婉,感叹人生的无常,这也算是虚构的东韵西律吧。回过头来看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有她的早期小说,再看茨威格的小说,以及追溯到鲁迅的小说,似乎都绕不开悲悯。他们的成熟和睿智似乎都不是在歌颂上,而是清醒地面向了苍生。所以,读茨威格的纪实作品,看鲁迅杂文,品封城日记,就有了对历史的穿越,反观虚构的文学,就显得无力而苍白了。
——2020年3月13日 于兰河畔
(本文系《禾颜阅车》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